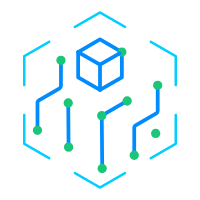44句歌德浮士德精选文案
歌德浮士德
1、近代欧洲社会在思想上回归古希腊审美观思潮的力量强大,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之后,人们都向往古希腊那种阳光明媚的生活。
2、主人公一生不懈追求,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宏伟气魄。它诉诸形象阐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矛盾发展的辩证关系,具有深刻的哲学内容。
3、作为人类的代表,浮士德概括了人类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了人性的双重性,其探索“囊括着人类全部的历史”。虽然浮士德历经挫折,但他积极探索,表现出向善的精神。其死后灵魂被上帝带上天国,彰显的是对其一心向善之精神的褒奖。此外,浮士德的身上也体现着善与恶、灵与肉的冲突。一方面,他不满足于既有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时常沉迷于名利、地位和权势之中,虽然最后摆脱了现实诱惑和个人欲求的束缚,但是他抵达理想世界的曲折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其人性内在冲突的存在。浮士德的矛盾展示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反映了人类探求真理的艰巨性以及歌德对人类终将走向至善的坚定信念。
4、当然并非诸如此类不能在舞台上呈现的个别场景,决定了《浮士德》同时是一部阅读剧,而是更重要的是,整部戏剧需要人们启动思考,“用心”去领会。按照作者自己所讲明的意图,读者需要自己去补充完整,去“衔接前后关联”;为理解整部作品,人们必须认识到前后的呼应,把作品当作一部“前后相互映照的整体”来读;同时还要加入读者自己的处世和人生经验,甚至需要读者“敢于超越自己”。
5、一个球正在向前滚动永远有一个触点的触碰在虚无的旷野中留下了自己的刻度
6、歌德反对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反对人的原罪必须依靠神的怜悯而自身无能为力。他认为人虽因袭罪孽,但人性中有善的胚芽,凭借着神的培养,可以自我救赎,走向崇高之路。《浮士德》中天帝与魔鬼在浮士德身上打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人虽然具有各种惰性和罪孽,但只要有向上向善的灵魂就可以得到救赎。所以,天帝对靡非斯陀说:“不妨把他引上你的魔路,可是你终究会惭愧地服罪认输;一个善人即使在黑暗的冲动中,也一定会意识到坦坦正途。”
7、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斗的精神历程。
8、再比如梅菲斯特,其老到的谈话艺术,体现在他可以自如地运用格律灵活的牧歌体,可以像变色龙一样,在格律上适应对方的讲话方式,一如他让格律符合自己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情境。斯巴达王后海伦的“古典”美也是音步之美。伪帝的营帐一场具有复辟特征,与之相应,台词不仅在内容上回溯到《黄金诏书》的条文,而且在格律上使用了过时的亚历山大体。即便是此处格律上的疏漏,或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明显的蹩脚、不流畅甚至是“失败”的韵律,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或是与角色相符,或是包含着可识别的意义。因此遇到这样的情况,断不可以为是格律大师本人力所不逮的结果。
9、《浮士德》的构思和写作,贯串了歌德的一生,1768年开始创作,直到1832年——前后一共64年。
10、诗剧大量用典,象征手法突出,表达了丰富的哲理。诗人用象征性的语言将深厚的哲理融入人物、事件之中,实现了形象性和哲理性的统一。
11、对靡非斯特这个人物的理解在当下比较全面了:有人将其视作一个浮士德需要不断克服、战胜之才能飞升上天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在浮士德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靡非斯特的影子,靡非斯特是浮士德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表面上的主仆关系掩盖不了二人的相互交融,他既是向善的阻力,又是一种原动力,他促进了浮士德向善的追求。残雪的《靡非斯特为什么要打那两个赌?》指出:作者写靡非斯特,是要向人类展示自己毕生的追求,是要将生命中的狂喜和悲哀、壮美和凄惨、挣扎和解脱、毁灭和新生,以赞美与嘲讽互相交织的奇妙形式展现在人间。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沉痛:人要绝对遵循理性来成就事业极其困难。在沉痛与颓废的对面,便是那魔鬼附体的逆反精神,是一种动力。丁谦的《西方文学中的伴生对偶原型》一文从“伴生对偶”出发,将主人公视作对偶中的两极,是资产阶级人性中两种力量的冲突与合一。
12、然而事实上,早在首演甚至出版前,《浮士德》剧就已广为流传:通过歌德自己公开朗读手稿的形式。对于剧本的传播这种形式如今已不多见。然而几十年之久,它都是《浮士德》传播的唯一方式(即便在作品出版和被搬上舞台后,歌德也终生保持了这一方式)。在大约在1797年创作的献词中,歌德写道:他们再听不到我将作的歌呤,/虽则开篇曾是唱给这些灵魂;/欢聚的友人早已是四散飘零,/可叹最初的应和已无影无踪!/我的歌将要面对陌生的观众……(行17及以下)
13、《浮士德》是一部宏伟的史诗。它是资产阶级整个上升时期的历史的艺术概括。别林斯基把它与《伊里亚特》、《神曲》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代德国社会的一面完整的镜子”,“是它的时代的史诗”。
14、仍然拥有的彷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15、《浮士德》是用诗剧形式写成的,全书共有12111行,题材采自十六世纪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浮士德原是个真实人物,生活在十五世纪。
16、他感叹“我们精神的翅膀真不容易,获得一种肉体翅膀的合作,可是,这是人人的生性”。浮士德的痛苦,来自这两种需求无法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的痛苦。
17、同样的艺术游戏也体现在用韵方面。比如在城堡内庭一场,浮士德与海伦的相遇相爱,是通过对韵这一媒介完成和见证的;又比如荣光圣母对格雷琴祈祷的回应,通过交叉韵的媒介表现出来。歌德在韵律艺术宝藏中汲取的养料,同样化用在《浮士德》中,使得韵脚在此不仅具有功能性,而且常常直接承载很多意义,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仰皆是。
18、《浮士德》是欧洲与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价值和最富影响的作品之一。同《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被誉为“名著中的名著”,既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压卷之作。
19、爱情悲剧之后,浮士德感到需要把人生的欲望放在更大的空间中,在政治上实现抱负。于是,他与魔鬼到了皇帝的宫廷,但皇帝却把他们视为弄臣,必须与现实同流合污才行。在现实政治中,要么作恶,要么放弃,浮士德最后选择了放弃。这一选择也正是歌德魏玛政治生活失败的象征。
20、而魔鬼挑唆少女哥哥瓦伦丁和浮士德争斗,瓦伦丁死于浮士德剑下。少女成了镇子的罪人,冬天,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得不到救助在雪中悲惨地死去。
21、“五四”之后,开始了对诗剧的翻译,并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歌德研究专著:冯至的《歌德论述》。其中的《〈浮士德〉里的魔》等两篇论文直接对《浮士德》进行了解读,文中将其看作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
22、说到浮士德精神,董问樵直接引用了悲剧人物的表白来分析其主要方面: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真理,重视实践和现实。杨武能的《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提出:浮士德精神非纯粹的德意志精神,而是整个欧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延续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欧洲精神的凝聚和结晶。张辉在他的论文《浮士德精神与中国化审美诠释》里比较了宗白华、张月超等人的观点后发现了审美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悖论:审美的来理解浮士德精神,并以之进行审美启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吁求,同时由于对审美作用的片面强调,可能伴随着审美本质的变异乃至异化,使人变成审美乌托邦里的“单向度的人”。
23、“很显然,自古以来,各国族最好的文学家、追求审美的作家,无一不致力于普遍人性的东西。就每一具体情况而言,无论那作品是历史的、神话的、虚构的,还是或多或少任意的,人们都会透过民族性和个体性,看到普遍的东西暴露出来。只有当人们让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民族的特殊性安于现状,只有当人们坚守一个信念,即真正的成就是因为它属于整个人类,真正意义上普遍的宽容才一定能够实现。
24、此类想象包含在那个广泛流传的、流光溢彩的所谓“浮士德精神”概念中,而这一概念则完全脱离了歌德的作品本身,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化的公式。1900年前后,出现一系列充满激情的口号式的书名:《浮士德式的人》《浮士德精神》《浮士德式信仰》《浮士德的天性》《浮士德的千年》等等。伴随这些著作,德意志使命感远播到近代的欧洲各处——当然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歌德所设想的方式:如前文所述,歌德曾设想,从魏玛条条街道通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25、《浮士德》是歌德的毕生力作,前后经过了60年,它属于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巨著之奠定了歌德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
26、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斗的精神历程。
27、本序言无意对整部《浮士德》做一个概述,而只是提纲挈领指出几点特殊之处,为以下的注疏给出基调。故而就“吸取外来财富”一项,在此仅以诗歌格律和文体为例加以说明。前者是一切语言规则的基础,对于后者会稍作展开。
28、作家、画家、前文提到的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都可谓得益于歌德吸纳而后又吐出的东西。如此得益的还有很多其他群体,比如神学家和哲学家,歌德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后又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可供思考的东西;比如语文学家和辞书编纂家(《德语字典》的编者格林兄弟,《歌德辞典》的编者);再如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见相关文本的注释部分)。
29、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
30、可是甚至连玛甘蕾也无法满足浮士德对享受尘世生活的渴望,他又开始了新的追逐。通过魔鬼摩非斯特与酒室小伙的饮酒作乐,歌德肯定了人类自身的现世享受。然而又通过玛甘蕾肯定了爱情的无私与纯洁。
31、饱含深刻的批判精神。通过浮士德的探索,作品批判了封建宫廷、教会和经院哲学等整个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精神支柱。同时,对资产阶级的殖民掠夺,残酷的原始积累,以及其自身种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等,都予以揭露。
32、 《浮士德》是一部长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的诗剧。它是歌德的主要代表作,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这部不朽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33、他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
34、歌德通过《浮士德》的悲剧告诉人们:人就在善与恶、欲望与现实之间挣扎和求索。浮士德的一生就是从尘世的爱欲中而奋力向善的境界追求的悲剧。浮士德在书斋中感到了生命浪费在知识上的可悲,人还没有活着就要死去,这是他必然走出书斋到尘世中体验万千缤纷事件的原因。当他听到地灵的启示,感悟到人无论如何伟大与卑微,其本质不过是生命而已,人作为一种活的生命存在就应精彩地生活。因此,他翻译《圣经》不是太初有名,也不是太初有力,而是“太初有为”。他的意思是人不是逻辑知识的堆积,也不是理性的筹划,人要体现生命创造化育之功,那么人之初就要奋发有为。
35、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1923)一书中称浮士德这个人物形象是西方近代整个文化时期的象征。他认为浮士德式的文化是“意志文化”。这种文化的动力就像浮士德不断“追求”那样,促进历史向前发展,而赋予行动的主体在世界和历史上以自我完成的目的。
36、歌德在此处借浮士德之口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说人生就是要造福人类,就是要行善积德,而是作为一个人必须精彩地活着,他要积极地去经历各种事情,去体验多样的情感,去探索人生奥妙——“人生就在于体现出虹彩缤纷”。人生活的多样可能性、存在的扩展和生命的张扬,才是歌德对人性的真正看法。
37、《浮士德》是歌德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巨著,这部诗体悲剧历时60余年创作而成,熔铸了歌德全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体验,是其历经毕生探索而得出的思想艺术总结,其它作品则是这部“巨大的自白的许多片断”,它也代表着当时欧洲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欧洲文学史上与《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并称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
38、作为戏剧实践者,歌德毫无疑问很清楚,《浮士德》的上演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且问题不只在于第二部的复杂,也不只在于整部剧本过长的演出时间。歌德本人作为剧院领导,自己在排练上演其他剧目时,也难得做到严谨地“完全忠于原著”,因此他宁可接受删减和改编的代价——至今人们见到的《浮士德》演出脚本大多经过删减和改编——也希望作品能在舞台上得以呈现。
39、浮士德毕竟是中世纪的书斋里走出来的,他身上仍有明显的旧的痕迹。他的性格充满矛盾,正如他自我解剖道:“有两种精神寓于我的心胸”,一个“执着尘世”,“沉溺于爱欲之中”;一个则要“超离凡尘”,“向那崇高的精神境界飞升”。
40、浮士德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看到上帝之水正淹没城邦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的无力如同梦魇里不能醒来的恐慌没有理想之光照耀现实如死水慢慢变腐如果以理性改造世界主义便是杀人恶魔人在秋千上不停地摇摆人生难有片刻的宁静上帝与魔鬼争夺灵魂按照约定开始人的旅程
41、为歌德之创作做出贡献的,大多是一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为方式、讲话方式反映到歌德这位伟大的人类观察者、形象塑造者的作品中。希腊人和犹太人参与了创作——希腊神话和犹太圣经奠定了《浮士德》的基础;除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外,还有无数其他人(在狭义或广义上)“共同撰写”了这部集体创作,他们有神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有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军事理论家,有工程师、技术员,有历史学家、语文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有建筑师、雕塑家;还有画家特别是素描画家,歌德或收藏有他们的原作或复制品,或通过他人描述得知他们的作品。很多作品都给予了他很大启发,为《浮士德》的语言和戏剧人物、动作、场景等提供了模式。
42、所有艺术都建立在艺术积累的基础上,没有任何一部艺术作品仅归功于某一个人的天赋。在1824年12月17日致冯·米勒总理大臣的信中,歌德写道:“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就”按理是属于作家的,“只有吸取他人财富化为己有,才会产生伟大作品。我不是也在(天堂序剧一场天主与梅菲斯特对话中)塑造梅菲斯特时吸收了约伯的形象,且(在夜晚和格雷琴门前的街道两场中)吸取了莎士比亚的小调吗?”
43、人们认为人应该在婴儿时就回到古希腊,接受古典美的熏陶,形成完善的人格,成年以后将这种人格带回以完善自己的民族。